返回目录:文章阅读

在马一浮看来,六艺不仅统摄中国一切传统学术,而且也统摄西方一切学术。既然性德是天地人生的根源,既然性德是人人所本来具备的,既然性德所流淌出来的六艺之道充盈于天地之间,既然一切都是六艺的体现,因此人类的一切思想无不是性德与六艺的不同方面的展示而已。当然,正如前文所强调的,这里所说的六艺并不限于作为经典的六经。
马一浮早年游学美日,广泛了解西方哲学思想,但事实上他对西学缺乏严格的训练与深厚的素养。不过,马一浮本于他的国学修养,对西方学术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洞见,那就是他认为西方哲学与文化“悉因习气安排”,因此“从来无人见性”。在马一浮的思想中,性德是最根本的思想基础,因此“不见性”就意味着西方思想遮蔽和失去了源头活水。由于西方在源头处有所差失遮蔽,于是影响到后来西方思想每走一步,都不能本真无妄,都是“习气安排”,最终走向封狭,使各学科“各有封执而不能观其会通”。正因为西方思想文化不能见性,不达本源,是性德运行的一种变异与遮蔽形态,所以以性德的全体开展为基础的六艺得以统摄整个西学。
西方二希(希腊、希伯来)传统开出哲学、科学、宗教等思想学术。因篇幅所限,在这里我们仅考察马一浮所提出的“六艺统摄自然科学”,看看他是怎样说明这一论题的。马氏认为,性德之流行,是通过“象”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有了“象”,而后才有“数”。象的周流、牵引、伸缩与出入,使易教得以成立。自然科学以数目、数量、时间、空间等为主要的研究范畴,这些范畴其实都是象的各种形态,因此自然科学与易教是相通的。但是话说回来,这些范畴,是由于自然科学对象数采取了一种现成性的观看领会方式,从而将其对象化、现成化、固定化。这是对本源的象数的一种执着与遮蔽形态。由此,象数的基础即性德隐退了,象数的流行性、涵摄性给消囿了,科学的工作便容易收缩为仅仅对对象化、固定化的象数的数学筹划、范畴界说。但是,只有奠基在一个性德开展出来的本源象数的流行境域上,对象数的现成化、固定化才是可能的。因此,自然科学不但与易教相通,而且也统摄于易教,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变异与衍生形态。科学有所封执,因此难以见性。
除了论述自然科学为六艺、易教所统摄外,马一浮还体认出哲学统摄于《易》、社会科学统于《春秋》、宗教统于《礼》等论题,今不详述。
马一浮所提出的六艺统摄西学、西学未能见性等判教论题,在熊十力以及后来的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处都能找到相应或相近的内容。熊十力曾有“性智”与“量智”之分,并指出由性智可建立玄学,由量智可建立科学。量智的构划以对象化、客观化为基础,并不能见性见体,如要见体,则需要靠性智。同时从根本上说,量智原来即是性智的发用,因此性智可统摄量智。可见,熊氏之科学不能见体之说,与马氏之说具有内在一贯性,只不过后者是在六艺与易教的背景下加以阐发罢了。后来牟宗三发扬熊十力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两层存有论(执的存有论与无执的存有论),并会通《起信论》一心二门(心生灭门与心真如门),建立起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会通西方科学民主(此属生灭门、执的存有论)的大综合。这也与马一浮六艺统摄西学、六艺统摄科学等判教观相接近。
但是在判教上,马一浮与熊十力、牟宗三也有差异。马一浮相当强调儒家六艺的本位立场,相当强调科学、哲学的虚妄性并过分排拒之,倾向于“摄用归体”的收摄性方向。相比之下,熊十力,特别是后来的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则在此基础上对科学与哲学等有所重视并有具体的考察,同时在某种程度与条件上对它们给予肯定,较倾向于“从体起用”的开拓性方向。现在看来,马一浮并不关注和辨析传统文化与科学的融通、曲通的环节与过程,而是一步到位、自说自话,这种取向在当代的背景下,明显是薄弱与贫乏的,其保守性与局限性也自不可掩。
摘自“大家精要”丛书之刘乐恒《马一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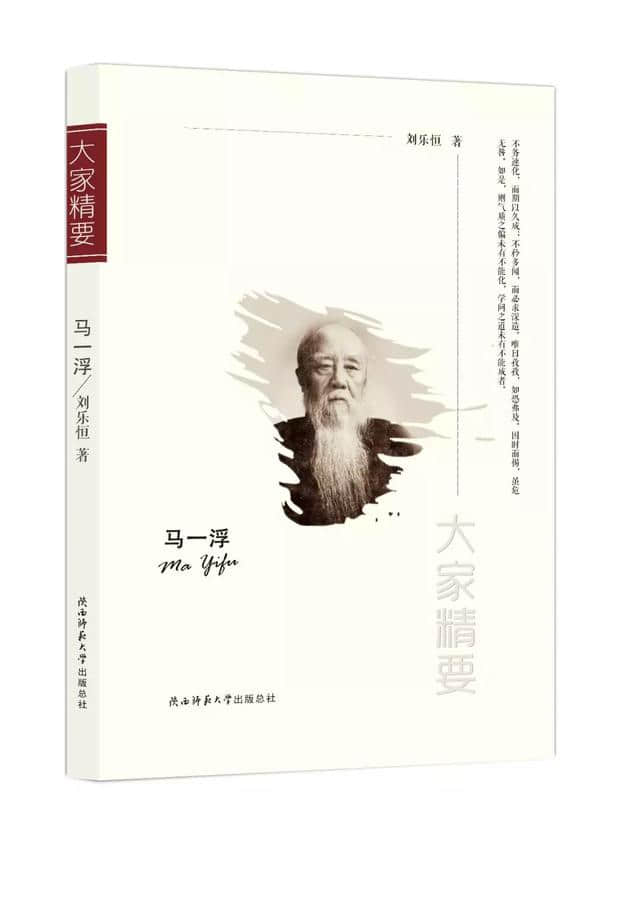
《马一浮》讲述我国现代著名思想家、诗人、书法家马一浮的生平以及学术成就。着重阐述他的现代新儒学成就——六艺论,从六艺作为意义机制、判教系统,六艺互摄论,六艺论的当代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展示出其发挥孔子仁学义蕴,试图解决近现代社会意义迷失的危机,安顿人们身心性命的学术初心。
作者简介
刘乐恒,1981年生,广东东莞人,哲学博士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讲师。曾访问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并在美国西肯塔基大学讲授中国哲学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