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目录:诗词赏析
当代作家 叶炜的长篇小说《福地》是他“乡土中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若将这部作品放在乡土叙事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来看,似乎没有多少新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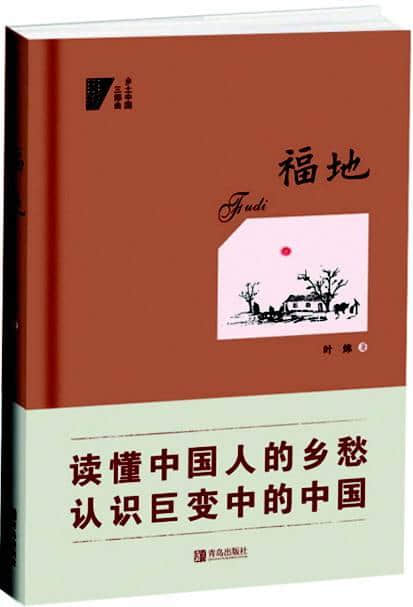
《福地》沿用的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众多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的基本框架,即将家族史与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政治发展进程融合在一起,把长幅的历史画卷浓缩为一个家族的兴衰存亡史,带有“小型化史诗”的叙述特色。
张艳梅曾在《从〈福地〉看叶炜小说创作的基本立场》中写道,“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受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历史题材小说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不再描写阶级斗争,不再塑造英雄形象,而是转向民间,通过书写家族史、村落史、个人史来解构历史、虚构历史、重构历史”。
《福地》即是如此。
在此种类型的长篇小说领域中,已经涌现出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张炜的《古船》等。在这样一个群英荟萃的文学大观园中,如何做到一枝独秀?叶炜携《福地》而来,用作品向我们证明——他确确实实做到了。
《福地》取材于苏北鲁南地区,以麻庄地主老万为核心,把万家三代人的命运作为主线,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武昌起义、军阀混战、国共内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文革等,通过麻庄这样一个窗口表现出来,在展示万家儿女各为其主的人生选择的同时,也暗示了被历史潮流裹挟着向前的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张艳梅认为,《福地》是“以一个村庄的平静喧嚣,一个家族的荣衰聚散,映射近现代中国复杂曲折的道路选择及历史进程”。

这部作品的基本框架虽然大家司空见惯,但在细节的安排和处理上处处显露着作者的独具匠心,这也使得《福地》在万紫千红的乡土叙事图景中没有被经典作品的光芒掩盖,反而大放异彩,有了更高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
一、天干地支纪年法
首先,叶炜没有采用当下通行的公元纪年法,而是巧妙地运用天干地支的方式纪年,并以此来命名各个章节。
提到天干地支,人们大多会想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知道这些字通常用来纪年、做字序,或做生肖属相。
天干地支的由来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商族,《诗经·商颂·玄鸟》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族人就根据“玄鸟生商”的传说,“用一种特殊符号记载他们祖先契十月孕育的过程……后来人们称之为天干。继而商民又用刻符记述了从子契到王亥,这一上古时期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生产生活情况……后来人们称之为地支。”
可以看出,所谓天干地支其实是“整个商民族、商部落起始的历史载体”,也是“中华民族的第一部史书”。天干地支谱写了商族的历史,《福地》讲述了麻庄的历史,麻庄的起源和天干地支的原始含义交相呼应。
小说中,因“大明朝廷采取了移民垦田的政策”,一批山西农民不得不迁移到苏北鲁南地区,机缘巧合之间选取了一块风水宝地,创建了麻庄。
麻庄的诞生很偶然,麻庄名字的由来也很偶然,由“嘛庄”到“麻庄”,带着几丝荒谬的味道,但正是这种偶然和混沌相融合衍化为自然,从而促成了村庄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息。
老槐树是麻庄历史的见证者,它跟随麻庄祖先们从山西洪洞而来,虽然它已在村子里扎根五百年,但它始终铭记自己祖先的方向,“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万家的子女们,为奸为党为宦为匪,因不同的命运而漂泊四方,但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他们都和老槐树一样未曾忘却根之所在。
麻庄有难,他们更是义不容辞,即使是糊里糊涂做了汉奸的万福,也是竭尽所能护麻庄周全;万喜为尼后与家人隔绝,无权无势无财无力,却也在深夜悄悄将半袋口粮放在家门口,帮助父亲渡过难关。
叶炜认为,作家的创作,归根结底是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还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福地》或许是叶炜的的一次寻根之旅。
祝家君在《甲乙丙丁是谁 说个子丑寅卯——解读天干地支》中,将十天干最初的刻符拆解开来,发现这十个符号与人的胚胎发育过程一一对照,“天干十字恰恰吻合了怀胎十月”。远古时期的商民用这种方式记载祖先契的孕育过程,以此铭记商部落的“根”。
相对的,叶炜在小说开篇就对麻庄的历史追根溯源,从老槐树到一粒种子再到山西,他寻求的不仅仅是麻庄的根,也不仅仅是自己的精神之根,更是以小见大,昭示着对整个中华民族之根的追寻。
二、民俗文化的描写
小说中也不乏对苏北鲁南地区民俗文化的描写,如过小年要辞灶,六月六为晒衣节,二月二龙抬头需吃“炒蝎爪”,夏至吃面,四月初八逛庙会,秋分吃秋菜等等,这些民俗镶嵌在小说的各个章节,为麻庄村民平淡的日常生活增添了喜气,也为整体的叙事格调增添了一抹亮色。

不过,诚如李新宇所言,这些民俗文化“没有多少可以炫奇之处;深掘文化,多属中华大路货。”但也正因为如此,没有特异之处的麻庄“具有某种普遍性,更多地包含了华夏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密码。”
而这恰恰与十二地支的原始含义——记述上古时期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生产生活情况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天干地支是商部落的史前史,反映的是氏族母系社会的中后期,也正是我们要追寻的“中华民族的远古历史”,叶炜用天干地支纪念并命名各个章节,将麻庄的兴衰存亡史嵌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当中。
曾经的麻庄处于世界边缘地带,像一方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麻庄不可避免地被拖入时代的洪流当中,历史的大浪淘沙溅起的沙石激荡起麻庄这片平静湖面的波澜,清朝覆灭,民国倒塌,麻庄靠着乡村独有的顽强生命力一次次挺过难熬的岁月,当历史回首,麻庄依然矗立在那里。
麻庄的生命力昭示着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源自商族的干支后来奠定了汉文字发展的基础,促成了我们文明的开端,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历经沧海桑田,绵绵不灭,几经兴衰却依然傲立。
三、人物形象的多面性
老万是《福地》的核心人物,也是麻庄的主心骨,《福地》讲述了麻庄的百年沧桑,也恰恰书写了老万的一生。
作为贯穿小说始末的重要人物,老万对于麻庄而言,既是一个守护者,也是一个统治者。叶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将老万塑造成一个穷凶极恶的传统地主,也没有将他表现为一个完美无瑕的英雄,“他既承载着中国农民的几乎全部的美德,同时也体现着乡土精英们身上的某些问题。”

战火纷飞时他临危不乱,是非分明,组建麻庄的自卫队,敢于同恶势力斗争,几次拯救村民于水火之中;日常生活里他又有先见之明,居安思危,灾荒时提前储备粮食,带领村民挖水井来确保日后庄稼的灌溉,以一己微薄之力守护麻庄,让它的血脉得以延续下去。
对内,面对背叛自己而与儿子万福私通的滴翠,他虽气愤却还是宽恕了他们,欣然接受了孙女万春;对于外来者香子,他也没有将对日本人的愤怒转嫁到香子身上,他怜悯她,在风声鹤唳的时代中尽力护她周全,最后毫不吝啬地为她置办嫁妆,像嫁女儿一样送她出嫁。
老万名“仁义”,他也的的确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仁义的准则,但同时也用不光彩的手段维护着仁义的颜面,来确保自己在麻庄地位的独尊。
老万丧妻后看上了王顺子之妻滴翠,在王顺子登门要妻时,用土地和大洋逼迫王顺子放弃了妻子,而后名正言顺地将滴翠收房。表面上看是王顺子贪恋财物而选择“要地,不要人”,实际上却是老万倚仗着地位和家财霸占了他人之妻,荒谬的是,老万的行为非但没有遭到王顺子的指责,反而因物质财富因素的介入而变得合情合理。
万福将十块大洋一块一块地递给王顺子时,“王顺子接一块说一句;谢谢老爷,连说了十次”。受害者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因钱财而对施害者感激涕零,乡村文化秩序因为物质权力的介入而变得暧昧不清。

对于背叛万家滴翠和嫣红,老万顾及到万家的颜面和世代累积的名声威望,没有驱逐她们,对外依然保持她们在万家的身份,对内却采取了古代帝王对待失宠嫔妃的方法,将她们打入“冷宫”,把滴翠和嫣红安置在后院的柴房;
而另一面,他又慷慨地为孩子起名,承认她们万家孙儿的身份,对待并非万家骨血的万乐,他也从未计较,视如己出。
老万身上的矛盾性恰恰映射了乡村文化的两面,叶炜以老万这个人物告诉我们:乡村文化既有包容万物的美好一面,也有藏污纳垢的黑暗一面,这才是真正的乡村。
就像老万,虽然他身上带有某些道德缺陷,但他依然是百姓眼中麻庄的主心骨,麻庄的守护人,文革时陆小虎一再煽动村民批斗老万,但村民心中涌现的往往是老万为了麻庄所付出的心血,即使他们确实受过老万的欺压,如王顺子的夺妻之仇,但内心并没有对老万的恨。
所谓故乡,无论它呈现哪一面,它都是村民心中一方安身立命的“福地”。

小说最后,万禄回乡省亲,万家兄弟谋划着要将抱犊崮等地改造成“一块洞天福地”,可是正如作者在文末写道,“几十年的时间,麻庄变了,一切都变了”。
麻庄不再是曾经贫穷落后的小村庄,也不再是人丁兴旺的家园故土,麻庄的年轻人早已离家四处打拼,留在麻庄的只有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
战火的硝烟,历史的变迁都未能让麻庄破败,而商品化经济却让麻庄渐渐变得空空荡荡,那么多的灾难,村子都顽强地挺了过来,却终究败在了物质的脚下。万家兄弟的计划能否实现?麻庄能否成为新一代人的福地?我们不得而知,但麻庄的现状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从开篇绣香产子到末尾万禄梦见兄妹四人回到母胎,万家由几代单传到四胞胎出生又到独苗单传,《福地》充满了轮回的意味,旧的生命结束,新的生命开始,在21世纪的今天,麻庄又会上演出怎样一番故事呢?或许作者可以以此为基础,再创作出另一番天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