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目录:佳句赏析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生于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子时(1619年10月7日),卒于壬申正月初二午时(1692年2月18日)。
王夫之自幼跟随自己的父兄读书,青年时期的他积极参加反清起义,失败后,晚年的王夫之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及后世遂称之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其在思想史、哲学史、史学史上的地位非常尊崇,后人对之评价也很高。
比如清代学者刘献廷就如是说:
王夫之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说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农,号蒋斋,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人。

南明永历时期形势地图

王夫之的故居湘西草堂,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曲兰乡湘西村菜塘弯
许多不同立场的人物也都从自己不同的角度高度评价王夫之。
比如保清卫道曾国藩就这么说:
独先生深閟固藏,追焉无与。……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亦为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则为长沙船山祠堂撰联曰:
训沽笺注,六经于易尤专,探羲文周孔之精,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文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

船山祠堂
甘愿为变法流血的谭嗣同这么说:
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天地大儒王船山》主要是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讲述王船山的心路历程。
并且赋诗曰:
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而积极参与反清革命的章太炎则这么说:
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
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端在于斯。
相反相成,或许端在于船山先生本身思想的丰富性和作为一个『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博大精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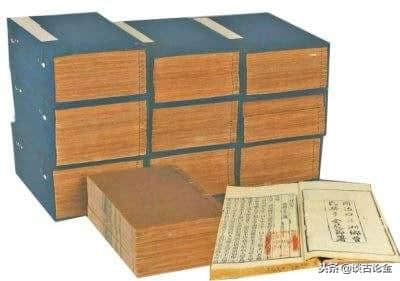
《船山遗书》100卷,同治四年曾国藩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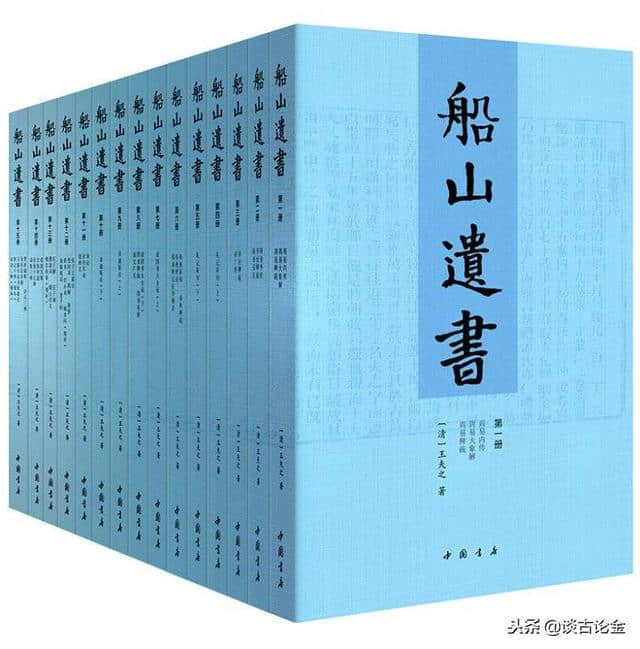
《船山遗书》(套装全15册),系同治四年版的简体字版
及至现当代,关于王夫之的评价也很复杂而深刻,以谈古论金粗浅的了解,侯外庐先生和嵇文甫先生关于王夫之的评价,就存在很根本性的冲突。
侯外庐(1903.02.06~1987.09.14,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先生认为:船山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暴风雨降临的时代,个人自觉,使得他产生了近世人本主义思想,船山思想,本质上反映了近代市民阶级人文主义的自觉,侯外庐引用王夫之《戒子书》中的文字证明他对工商并无偏见:
能士则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
然而,同样研究王夫之及其思想的嵇文甫(1895~1963,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当代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哲学家,郑州大学首任校长,历史学系的创始人)先生则不同意侯外庐的古观点,他从王夫之的著作中找到『国无贵人,民不足以兴;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任子贵于国,而国愈偷;贾人富于国,而国愈贫。任子不能使之弗贵,而制其贵之擅;贾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夺其富之骄』,指出王夫之对于商业和商人的观点和传统的『以末致财,用本守之』观点并无不同,也就并没有领先于时代或曰代表新兴的市民阶层的一面。
嵇文甫先生进一步指出王夫之在评论前秦苻坚统治时期富商赵掇的僭越行为时,申论中国夷狄之辩,君子小人之辩,他根据孔子斥樊迟,连农圃都不以为然,商贾更被他认为是利欲熏心、沉沦财货,绝对不可以让他们居君子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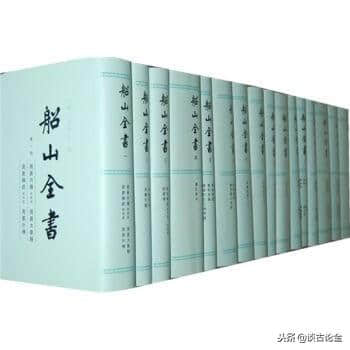
王夫之著书320卷,其著作编入《船山全书》。
嵇文甫先生的引证主要出自王夫之《读通鉴论 汉高帝十四》里的一段议论:
国无贵人,民不足以兴;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任子贵于国,而国愈偷;贾人富于国,而国愈贫。任子不能使之弗贵,而制其贵之擅;贾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夺其富之骄。高帝初定天下,禁贾人衣锦绮、操兵、乘马,可谓知政本矣。
呜呼!贾人者,暴君汙吏所亟进而宠之者也。暴君非贾人无以供其声色之玩,汙吏非贾人无以供其不急之求,假之以颜色而听其煇煌,复何忌哉!贾人之富也,贫人以自富者也。牟利易则用财也轻,志小而不知裁,智昏而不恤其安,欺贫懦以矜夸,而国安得不贫、民安得而不靡?高帝生长民间而习其利害,重挫之而民气苏。然且至孝文之世,后服帝饰如贾生所讥,则抑末崇本之未易言久矣。
这段文字言辞精警,掷地有声,从对权钱勾兑、官商结合造成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的抨击来看,也确实揭露出了问题的本质,但是无论是『贾人富于国,而国愈贫』,还是『贾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夺其富之骄』,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认知的偏差和偏见,不脱传统『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藩篱窠臼,而对『高帝初定天下,禁贾人衣锦绮、操兵、乘马,可谓知政本矣』以及『高帝生长民间而习其利害,重挫之而民气苏』的揄扬和歌颂,也只能说是看对了病却开错了方——诉诸权力哪怕是所谓的圣君贤相来抑末崇本打压商贾,和追求一个公平均富的社会的目标,其实是南辕北辙、抱薪救火。
王夫之这样的议论当然不是书生意气、空发议论。
当余生只剩下著书一事的时候,王夫之孤独地写,没有纸笔,就找门人和亲友去借,写完了,把书送给人家(诸种卷帙繁重,皆楷书手录。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船山先生在世时,除了在青年时期曾经刻过一部诗集之外,没有一本著作付梓,当时能读到船山先生这些呕心沥血文字的也寥寥无几,可他还在写,和古人沟通,和可能并不存在的读者沟通,艰苦卓绝,莫过于斯;苦心孤诣,无以复加。
一个一生悬命、而又贫病交加的学者,对富商大贾,特别是官商勾结、欺压良善的富商大贾不以为然,从情理上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春秋责备贤者,则不得不为船山先生惜,因为他的这些议论多少还是不周延不完美。

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地学家和音韵学家顾炎武

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黄宗羲
前面我们提到过,后世以至于今天人们把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但严格来说三人的立身行事和做派风格并不相同相似,顾炎武当然也抗志不屈、孤明独发,但是他在当时就得到顶尖学人的普遍认可;黄宗羲也并不寂寞,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影响颇大的学派,后来清廷开局编撰《明史》,都是以黄宗羲的门人子弟为骨干团队。
只有王夫之,辟地船山,一个人那么孤独地写着、写着、写着……。
因而,当亭林先生(顾炎武)亲自下海经商以至于『家累千金』(他的经商也是在为反清事业筹措经费),当梨洲先生(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时候,王夫之却和一个生机勃勃的崭新时代,生疏隔膜了起来。
虽然这一点也丝毫无损于他的伟大。
谨以此文,纪念我最亲近的湖南人、英年早逝的老同学李翌先生。